时间:2020-08-18 03:25:49 来源:搜狐教育-搜狐作者:山东省胶州市

文 | 莉萨·乔布斯
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之女
本文摘自《小人物:我和父亲乔布斯》
学院君说:现在正值暑假,是亲子陪伴的好时光。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的这个故事,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女儿萨利在她父亲病故之前的回忆,更是她与过去和解的成长故事,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,能够唤醒爸爸妈妈们对亲子陪伴质量的关注。

父亲病重期间,偷拿父亲的东西
在父亲癌末的探病期间,我持续在屋内到处偷拿小东西。我打电话给妈妈,把我在做的事告诉她。我希望她宽恕我。我希望她为我破例放宽不可偷窃的规矩,就这一次就好。我希望她说:乖女儿,那些东西你全部都可以留下来。
但是她说:“你要把他们的东西还回去。这很重要,你不可以偷东西──这就象是贝瑟芬妮(Persephone,希腊神话人物)。”用神话故事来比喻很像她的作风。“你知道吧,吃了石榴籽的那个人。”
我记得她被带到冥界,不该碰任何东西,但她忍不住吃了石榴籽,因此受到惩罚,每年有一段时间必须待在冥界,据说这是冬天的由来。我努力回想故事中她吃了几颗石榴籽。
“多少并不重要。”妈妈说。
“重点是她因为拿了石榴籽,所以被困在那里。她在冥界偷窃,分食那里的东西,于是也被那个世界给束缚。”
“所以呢?”
“你如果留下那些东西,你也会被那个家给束缚。那不会让你自由,反而会把你绑在那里。”贝瑟芬妮的故事当然也是一则母亲与女儿的故事,母亲在女儿离去的那几个月,因为悲伤而使大地荒芜。
我逐次把偷来的东西放回去,因为数量太多,没办法一次全部带去。我用枕头套包住碗,免得碰撞出声。我把唇釉放回浴室的架子,乳液放回二楼橱柜,鞋子放回更衣间。我发现归还偷来的东西而不被逮到,跟最初偷拿一样困难。
这一次探望,我爸看起来并不特别想看到我。他叫我离开房间,好让他跟弟弟一起看电影。他已经无法走路,也不能进食,但我仍妄想般地相信他还会活很久。
他病了这么久,久到我都没有发觉,这场病不知何时已迈向死亡。我回避他的房间,只偶尔强迫自己进去看看,而且总是希望我进去时他已经睡着了。那次探望的最后,我心想我大概不会再回来看他了,因为每次都令人空虚不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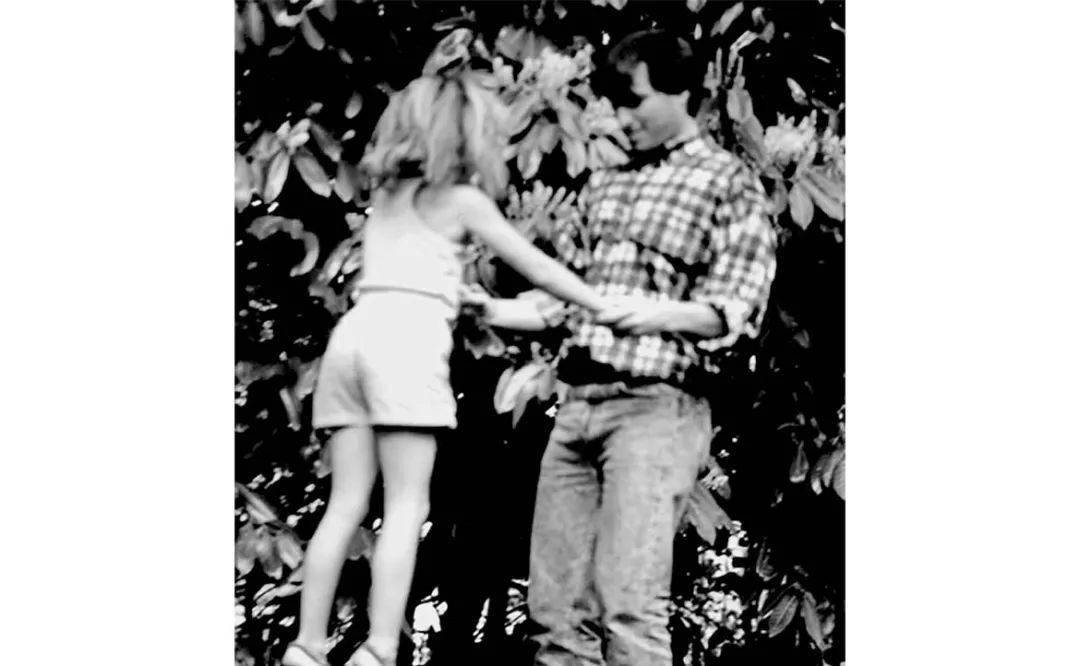
“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”
但一个月后,他传简讯给我──他平常不会这么做。他请我周末过去看他,劳伦娜(乔布斯的太太)和弟弟妹妹那个周末不在家,我从旧金山机场搭轻轨去帕罗奥多。
我很怀疑这趟旅程和其他几次能有什么差别。
我在加州大街站下车。城镇看起来无事经过也无事发生,马路直得像机场跑道,通入苍郁的山谷深处。我走艾玛街下方的人行道,在金黄阳光中从另一头冒出来,再经过公园和松树。这一带的房子都紧挨着土地。
这 6 个月来,我持续服用小剂量的可那平锭,这是一种抗焦虑药物,每天服用 0.25 毫克,宣称能减缓大脑杏仁体的逃避反应。虽然我爸曾坚持,或许就是因为他坚持,要我试试精神类药物,这种药物以前在我眼里反而并不吸引人──两者我都从来没有用过。但每个月搭飞机来回探望他,研究所也正逢毕业前夕,妈妈又生病缺钱,我发现自己不能专心,做事和说话愈来愈快。
我出现一种狂热的特质,希望让他人分心,而不用暴露我自己。我局促不安、戒心变强,而且很不自在,深怕我爸会说出一些可怕的话,然后就死了,所有疑虑都无法解答。
电影里常有垂死之人道歉的一幕,但这是现实人生。
我走进屋里,停在我爸书房的门槛前,这里现在改成他的寝室。里面有一张艾格顿(Harold Edgerton)拍摄的照片,是一颗苹果被子弹穿过,弹孔周围的果皮磨损。

我绕过转角到他房间,他用枕头垫着坐直身子,两腿苍白细瘦,像两根毛线棒针,抽屉柜台面摆满裱框照片,每一帧都斜过来面向他的床,抽屉柜有两排等宽的抽屉,后来我会看到每一格里面都是他整理过的艺术作品和摄影照片,他一个人,醒着,好像在等我,他对我笑了笑。
“我好高兴你来了。”他说。他的温暖令人放下戒心,眼泪从他脸上滑落。
他生病以前,我只看他哭过两次,一次在他父亲的葬礼,另一次是在电影院看《天堂电影院》看到最后,当时我还觉得他在颤抖。

“这会是你最后一次见我。”他说。
“你得放手让我走了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但我不太相信他的话,我也不会相信他再过大约一个月后就走了,对于他会活多久,我的想法始终模糊不清,我傍着他在床边坐下。
“你小的时候,我陪你的时间不够多。”他说。“真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。”
“没关系了。”我说。
他是这么的虚弱又脆弱。我在他床上这一侧躺下,脸朝着他。
“不对,有关系。我没有花够多时间陪你。”
“我应该要花时间的,现在已经太迟了。”
“我们大概没遇上对的时机。”我说,但说出口的同时就连自己都说服不了。事实上,我最近才意识到我的好运:我有幸在他还没大红大紫以前就认识他,他还很健康可以溜滑轮,我曾经想象比起陪我,他花了更多时间陪伴其他每一个人,但我现在不再敢断言了。
他看着我的眼睛,泪水涌上眼眶。
“我欠你一回。”
我不确定该怎么理解这句话。那个周末,他一遍又一遍重复:“我欠你一回,我欠你一回。”我在他小睡之间进去看他,他总是哭着说。

我真正想要的、我真正感觉亏欠的,是在他爱过的人之中拥有一个清楚的阶位。
除了每 6 小时轮班一次的护士,屋里只有我和他。有一些他不认识的人登门求见,带着包裹或空手在花园徘徊,陌生人恳求与他说句话,还有一名男子走进围篱栅门,说他远从保加利亚飞来只为了见我爸一面。成群的人聚集在侧门,相互交谈,不久又各自散去。
“你记得你做过的梦吗?”
我躺在他床上的这一侧。他睡睡醒醒。
“记得。”
“每次都记得?”
“大部分。”
“你都梦到什么?”
“大部分是工作。”他说。“想要说服别人某件事。”
“什么样的事?”
“一些点子。”
“你在梦中想到的点子?”
“有时候是。但通常我在梦里都说服不了他们。他们常常笨到听不懂。”
“你很多点子都是那样来的吗?在梦里想到?”
“对。”他说,然后又睡着了。

(拿着象征性的iPod和iMAC的乐高乔布斯)
“你没邀请我参加哈佛周末,只寄来账单”
隔天我陪他去医院输血。这件事花了几乎一整天,因为他太虚弱走不动,必须由人协助从轮椅抬上车,再抬上轮椅,再推进医院,再抬上轮椅,再抬上车,再换回轮椅,最后再回到他的床上。
血袋里的血色深浓稠,看起来像糖浆冒充的德古拉的血。院方从一台乍看像冰箱的机器里拿出一条加温过的毯子给他,他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,然后又发冷。
我坐在病房里的一张椅子陪他,听着机器嘶嘶作响。我很好奇他输的是谁的血。我很想问,但我不想引来注目。他大约每隔 10 天就要输血一次,每次要花好几个小时,结束之后,他脸上比较有血色。
输血快结束前,我跟一位护士说:“他好像会冷。”
“我很好。”他说。
我坐在角落的椅子等他。
“我觉得他可能会冷。”几分钟后我又说了一遍。
我能感觉到通风口吹出阵阵冷风。
“我没事。”他说。
之后我因为一些原因要离开病房一会儿,等到我被叫回来,坐回角落的椅子,护士拿了一条毛毯给我。
护士说: “ 他说你会冷。 ”
我都没发觉我真的会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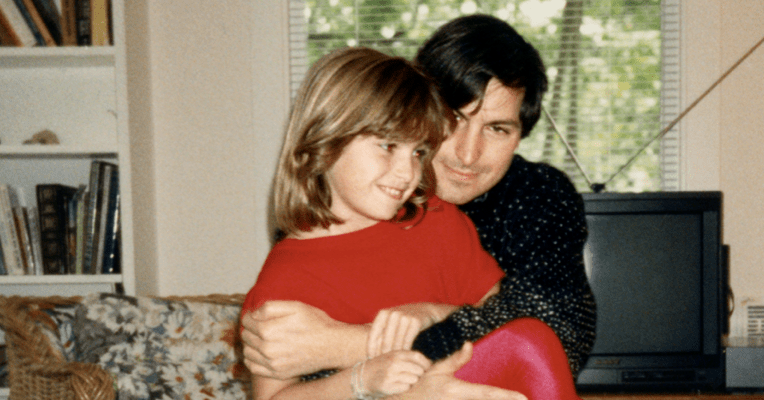
“我很抱歉没多花时间陪你。我真的很抱歉。”他从病床上说。
“我猜你太投入工作,所以没寄电子邮件也没回我电话?”
他很少回覆我的邮件或电话,也不记得我的生日。
“不是。”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不是因为我很忙。是因为我气你没邀请我参加哈佛的周末。”
“哪个周末?”
“新生入学周。我就只收到学费账单。”他说,话中带了哽咽。
大学入学。我后来想起来,当时 18 岁的我小心翼翼地安排我爸妈错开,他们不想同时到场,我的老师也帮忙协调,最后我们决定,双方也都同意,入学那个周末妈妈先来,他过几个星期再来。那时他也同意这样子最好。
“你为什么不跟我说?”
“我不太擅长沟通。”
“我很希望能收回决定,或是改变决定。”我说。
这看似很不可能,甚至有点离谱,我们多年来的关系竟然得归罪于一个周末。我不相信,我原本设想他有过人的智慧,但盼望挽回错误的将死之人,不一定能清醒地反省。
我不接受这个说法,我不接受一个邀约、一个周末,就能合理化他这 10 年来几乎断绝音信,合理化他在我大学最后一年拒出学费。
那些年间,我时常端详我的掌心,我应该过上好的人生──这才是我的掌纹代表的意思。

“要是我们有一本说明书就好了”
我还记得一年前,妈妈来纽约探望我的情景。她克服了令她脆弱的病痛,正在慢慢康复,她的听力受损,我们傍晚时分出外散步。
西四街和查尔斯街交会处,红砖排屋笼罩在夕阳下。妈妈和我停下脚步,一起凝望着红砖屋。那些日子里,我们渐渐有一种幸存者的感觉,我们熬过来了,我们会快乐的。
“话说,你真的会读手相吗?”我终于鼓起勇气问。
“算吧。”她说,一抹浅笑代表她说谎。
“我是说,你真的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吗?”我希望她说曾经在印度遇到高人,或是读过鲜为人知的书。
“你需要合适的故事。我们需要从身在之处去向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我不知道除了故事以外,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去到那里。更何况,我说的那些事,全都是事实。”
在他家中的那天傍晚,他用平常呼唤护士的虚弱声音唤我进去。
装着全静脉输液袋的背包马达正在运转,像绕着铁轨的玩具火车一样发出喀答喀答的声音,乳白色的液体流进他的静脉,他躺在床上曲起膝盖,垫着枕头。他异常地瘦,很难看着他,而不被他的四肢和枯瘦的脸夺去注意力。
“我们先前聊到的事──”他说。
我很意外他居然会提起之前关于情感的对话,他从没对我做过这种事。
“我想说句话:那不是你的错。”他哭了起来。
“要是我们有一本说明书就好了。要是我聪明一点就好了。但那不是你的错,要责怪的人不是你。我希望你知道,那半点都不能责怪你。”
他非要等到生命快消逝了才想道歉。我一直在等这句话,就象是清凉的水流过烫伤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哭着摇头,坐起身,把头埋进双手。
由于他体重骤降、全身缩水,双手看起来大得不成比例,脖子细到彷彿支撑不住头颅,彷若罗丹的加莱义民雕像。
“我真希望能回到过去,我希望可以重新来过,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能做什么?真的已经太迟了。”他哭得全身颤抖,呜咽哽噎,我希望他停下来。
之后他又说了一遍:“我欠你一回。”
我依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,只是一直坐在他的床边,即便此时此刻,我还是不太能相信这一切,我想象他如果奇迹康复,一定会回复原样,忘记现在曾发生的事,回头依然像从前那样子对我。
“至少我现在在这里啦。”我说。
“也许,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,我们可以当朋友?”这也是一记轻柔的反击:我们只会是朋友。然而事实上,在接下来几个星期乃至于他死后,我最哀痛的就是我们错失了做朋友的机会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“但是对不起,我欠你一回。”
自从归还偷来的物品以后,我没再拿走别的,但依旧会留意其他我想要的东西,现在那股匮乏感也干涸了。我再也没有想偷东西的念头。
其他家人回来了,屋里人声熙攘。吃过饭的傍晚,妈妈和我单独坐在餐桌旁。要是前几次探望,这种时候我一定会跳起来去洗碗,但这一次我坐在原位没动。
“他找我说话。”我说。“我们交换了重要的话,很有意义的话。我觉得好多了。”我以为她会问我交谈的内容,但她反而起身走到水槽旁洗碗。
“我不相信临终前的告白。”她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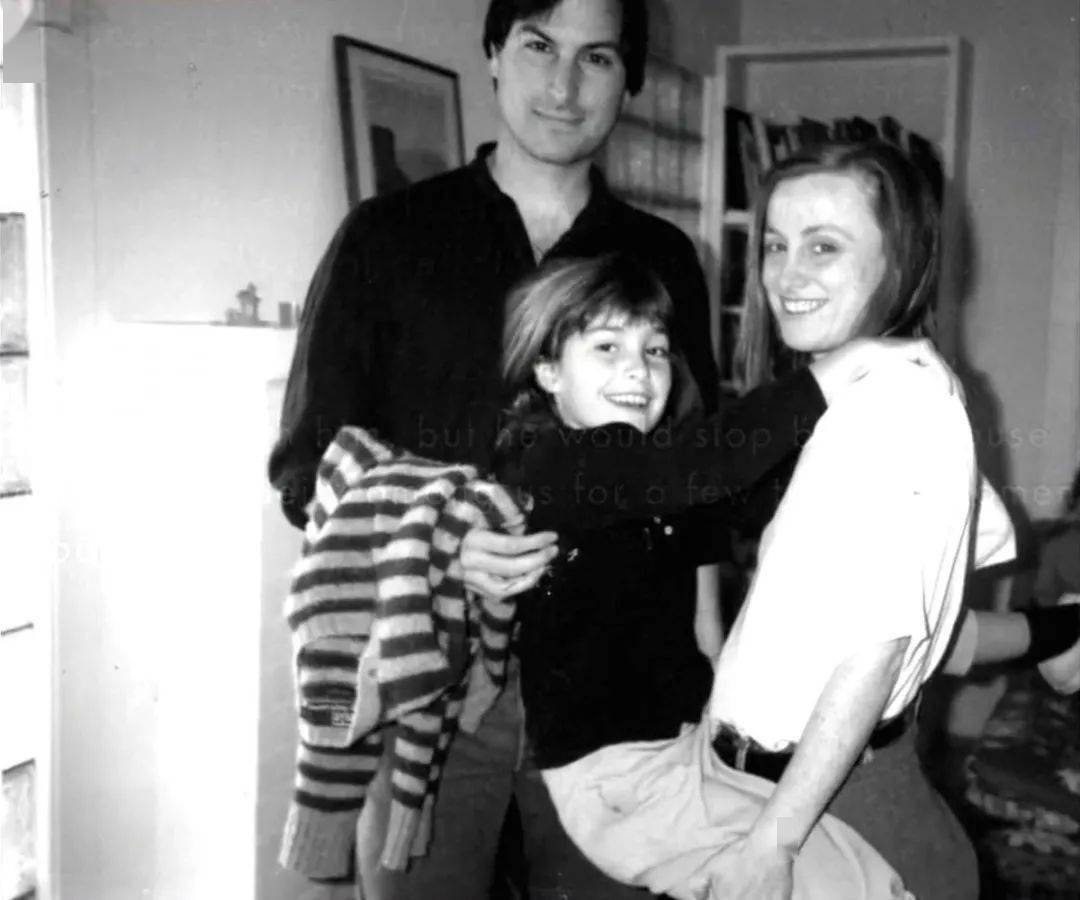
资源领取| 点击文末“在看”,并长按下方二维码,我们会把 10部暑期必看电影的观看方式发送给您。
免费课程天天领!《提升孩子表达力的9堂故事课》,配合趣味案例故事和实用理论,由浅入深,帮助孩子提升表达自信与感染力! 限量100份,先到先得!
点击即可领取
↓↓↓↓
责任编辑:
本文网址:http://www.gaoduanedu.cn/yuer/46319.html
声明:本站原创/投稿文章所有权归【高端教育】所有,转载务必注明来源;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不代表【高端教育】立场;如有侵权、违规,可直接反馈本站,我们将会作删除处理。
推荐文章
热文排行
热门标签
联系我们
服务热线 :027-51118219
业务 QQ :1440174575
投稿邮箱 :1440174575@qq.com